劉尚希指出,不宜過度擴大地方專項債規模,這可能造成對市場投資的擠出效應。建議2020年減稅降費可由中央財政承擔,以減輕地方負擔,相應適當擴大2020年赤字規模來彌補減收缺口。
疫情對我國經濟造成沖擊,隨著疫情在世界范圍的蔓延,其負面影響可能放大。為了對沖疫情影響,促進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,宏觀政策力度需要加大。
其中,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。圍繞積極財政政策如何發力,市場機構有諸多建議,包括加大減稅降費力度、提高赤字率、擴大地方專項債規模等。
我國政策空間依然充足,但空間也在縮小。像2019年2萬億大規模減稅降費,帶來部分地方財政的短收,多個省份出現了財政收入負增長。而今年受疫情影響,一方面企業經營困難會影響其稅收貢獻,財政收入增長余地更小;另一方面企業困難加大,需要財政加大支持力度,這會進一步加劇地方財政收支矛盾。
如何看待疫情對經濟的影響?財政政策如何發力穩經濟?如何應對地方財政困境?帶著這些問題,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。
劉尚希指出,包括減稅降費在內的宏觀政策,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在減弱,需要推進重點領域改革,來提振市場信心,進而更好地拉動經濟。不宜過度擴大地方專項債規模,這可能造成對市場投資的擠出效應。他還建議,2020年減稅降費可由中央財政承擔,以減輕地方負擔,相應適當擴大2020年赤字規模來彌補減收缺口。
高度不確定性下需要新預案
《21世紀》:2月數據陸續公布,當前怎樣衡量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?中國疫情防控工作不斷取得積極成績,但疫情又在全世界范圍內蔓延開來,WHO確定其為大規模流行病,這會對中國經濟造成什么影響?
劉尚希:衡量疫情對經濟的影響,要放在全球來看,放在中國來看已經遠遠不夠。按照世衛組織的說法,這次疫情是全球大流行,風險級別是最高的。
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,全球產業鏈、供應鏈都會受疫情影響。以前疫情防控主要在中國,會造成我們出口交貨的不及時。現在疫情在全球蔓延,其他國家疫情越來越嚴重,國產化還不能替代的零部件、原材料等進口會受到影響,有些產品出口也會受到影響。當然,與抗疫所需產品相關聯的出口會擴大,但無法彌補全球經濟下挫的負面影響。
當前國內和全球都受沖擊的局勢下,疫情對經濟的影響程度在加深,風險也在升級。
《21世紀》:這是否會對我們完成2020年既定經濟社會目標造成影響,尤其是2020年GDP相較2010年要翻一番的目標?
劉尚希:面對高度不確定性,毫無疑問應該實事求是,對2020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、和宏觀政策目標,應該要有新的預案和做出新的考慮。
經濟增長合理區間應瞄準就業目標
《21世紀》:中央明確,宏觀政策要加大力度,防止經濟運行滑出合理區間,防止短期沖擊演變成趨勢性變化。當前,宏觀政策的著力點應該放在哪里,如何防止滑出合理區間?
劉尚希:經濟增長的合理區間,應該瞄準就業目標。能保證充分就業、高質量就業、平等就業的經濟增速,就是合理的經濟運行區間,單就經濟增速本身無法判斷其是否合理。
我們一直強調,發展要以人民為中心,核心是要解決人的問題,所以經濟發展應以“就業狀態(包括就業充分、穩定、平等)”改善為中心。經濟增速定在哪里要視情況而定,只要有較高質量的就業,經濟增速高一點、低一點都不是問題。就業狀態的改善事關經濟和社會兩個方面,是我國高質量發展的基礎。
《21世紀》:2019年我國城鎮調查失業率雖有小幅攀升,但仍在預期范圍內。在人口老齡化、服務業占比不斷提升的背景下,就業問題值得擔憂嗎?
劉尚希:在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,就業不存在總量問題,主要是結構問題。
隨著我國服務業比重不斷提高,這能吸納相當規模的就業,但制造業的“機器替代人”的進程,部分就業崗位隨之消失。就業的結構性矛盾,在數字化轉型、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可能會愈發凸顯,加之人力資本積累在城鄉間差距較大,像農民工很多都只有初中以下學歷,對于低學歷、缺乏勞動技能的群體而言,未來找工作會越來越困難。
當前,高校畢業生也是很重要的群體,教育機構的專業設置如何更好地與現實需要匹配,怎么更好地與高質量發展、數字化轉型、產業升級相匹配至關重要。這需要加快深化教育體制改革,以此來增強人才培養機構與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相匹配的自適應能力。
結構性就業矛盾,可能會成為疫情之后的頭號公共風險。就業問題一邊連著社會,一邊連著經濟。居民收入來自就業,加上收入分配的問題,如果造成社會階層快速分化,可能帶來其他社會問題。
勞動力是生產要素,從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,結構性就業矛盾意味著部分勞動力出現閑置,同時部分企業招不到人,生產線無法滿負荷運轉。這種資源的低效配置,會影響經濟產出,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。就業的結構性矛盾會拖累經濟增長,在這種條件下,任何經濟刺激手段、宏觀政策都無法發揮作用。
在疫情沖擊下,可能有幾千萬人自愿待業,因為擔心染病,而選擇待在家里,這會影響他們的收入。與此同時,企業招不到人,選擇漲工資吸引更多人來,可能帶來用工成本的進一步上升。疫情下,就業風險在加大。
赤字空間沒有看起來那么大
《21世紀》:2月份很多企業未能正常開工,3月份還在積極推進復工復產,加上疫情期間允許困難企業稅款緩繳,以及2019年大規模減稅降費的翹尾因素,地方財政收入是否會受到很大影響?有什么舉措可以應對財政困難?
劉尚希:地方財政現在非常困難,不是一般的困難。大部分地方主要靠中央的轉移支付過日子。中央的錢從何而來?從較發達地區來。這意味著全國財政困難整體加劇。
在這種情況下,中央、地方政府都要過緊日子。政府剛性支出在加大,但財政收入增長很有限,需要對現有支出按照輕重緩急來排隊。當前首先要保證疫情防控的經費開支,再就是地方保基本民生、保工資、保運轉的“三保”支出。現在壓縮一般性支出的空間越來越小,其他項目支出也要有保有壓,要趁這個機會加快調整財政支出結構。
調整財政支出結構,和政府機構改革是一體兩面的。近年來,放管服改革取得一定成績,但政府職能轉變推進起來仍然困難重重,在這種情況下,要優化政府支出結構也是比較困難的。
當然,地方政府還是可以想一些辦法,比如盤活公共資產和資源,來緩解當前的支出壓力。另外,很重要的是借助市場力量,部分原本政府提供的服務,可以讓市場來參與,避免政府直接投資帶來的壓力,有的可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來實現。
還應該鼓勵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(PPP模式),地方專項債規模的擴大實際擠出了部分PPP項目,可以通過市場化改革的方式,通過規范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來緩解當前財政支出壓力。
這種情況下,2020年的赤字要擴大一些。但實事求是地講,我國赤字擴大的空間,并沒有表面看到的那么大。
減稅降費下還需加快改善營商環境
《21世紀》:外界對于更積極有為的財政政策有頗多期待,提到最多的是呼吁加大力度減稅降費。目前,階段性降低企業社保繳費,獲得較為普遍的歡迎。后續減稅降費該如何推進,其提振經濟的效果如何?
劉尚希:疫情期間,一些企業沒有營業收入、增加值、利潤所得,稅源都沒有,減稅對于休眠的企業沒有實質意義。但是,社保減費是有用的,因為員工工資要繼續支付,減少企業社保繳費,相當于減少企業的固定支出,對于企業維持資金鏈、維持生存是有幫助的。
疫情過后,減稅降費有一定作用,但也需要配合企業預期改善等,才能較好地提振經濟。從實際情況來看,減稅降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在減弱。像2019年2萬多億減稅降費,拉動經濟增長0.8個百分點,去年GDP規模接近100萬億元,也就是說2萬多億減稅降費帶來了不足8000億元的經濟增量。
減稅降費是能減輕企業負擔,但企業是否增加相應投資或支出,更重要的是取決于企業預期和企業信心。影響企業預期的因素有很多,很重要是預期利潤率,還有營商環境是否公平,生產要素、金融服務供給是否平等、充分,民營企業“彈簧門”“玻璃門”現象是否減少等。
如果體制環境改善了,投資者、民營經濟有信心了,減稅降費的作用就很明顯。如果只是減稅降費,其他方面沒有改善,稅收乘數效應會非常低,可能還會給財政帶來很大壓力,這樣的政策“性價比”很低。
不宜過度擴大專項債規模
《21世紀》:中央明確要擴大專項債發行規模。部分機構建議將2020年專項債規模提升至3萬億元,用以支持基建、新基建工程。擴大專項債規模,對提振經濟能起到什么作用?
劉尚希:一味地擴大地方專項債的規模,不是很好的辦法。符合地方專項債的項目,需要有足夠的現金流,這樣的項目越來越難找,部分地方出現了“資金等項目”的現象。部分專項債項目,可以交給市場來做,一味擴大專項債規模還可能擠出市場投資。
擴大專項債規模,能增加投資支出,進而拉動經濟增長。這是需求刺激政策,在疫情條件下,物流尚未恢復、復工復產還在過程中,需求刺激政策是無效的。等到疫情過后,拉動基建投資的政策,也面臨乘數效應下降,拉動作用越來越弱的狀況。我們測算的政府投資乘數小于1 ,這與2009年大相徑庭。
2020年財政支出結構應該優化,不宜過度擴大地方專項債規模,建議2020年的減稅降費由中央財政承擔,不要讓地方來分擔,因為減稅降費會加大地方財政平衡壓力,可以適當擴大2020年赤字規模,來彌補減稅降費帶來的減收缺口。
此外,針對當前尤為重要的就業問題,積極財政政策應該發揮作用。擴大政府投資當然能解決一定就業問題,但要解決當前結構性就業矛盾,并不是單純上基建項目就能實現的,尤其是對年輕人就業,其作用很小。
只要改革立馬可以見效
《21世紀》:宏觀政策的作用有限,是否需要其他舉措加以配合?
劉尚希:面對經濟、社會問題相互交織,國內、國外風險彼此疊加。我們這個社會共同體變得越來越復雜了,經濟體系也越來越具有不確定性,單一的宏觀經濟政策,政策效用的確在減弱,解決不了多少問題。
宏觀政策要和改革措施結合起來,通過改革來改善市場預期、增加投資者信心。像國企混改、支持民營經濟發展、土地制度改革、財稅金融體制改革等,這些重要領域的改革,有實質推進,能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。
認為改革短期沒法見效的想法是錯誤的,只有改革才能增強信心,立馬可以見效,改革才能從根本上扭轉信心不足的問題。
解決任何一個局部的問題,防范化解任何一類公共風險,都需要從整體著眼才能奏效。當前形勢下,完善制度,提高治理效能變得更為緊迫。
標簽: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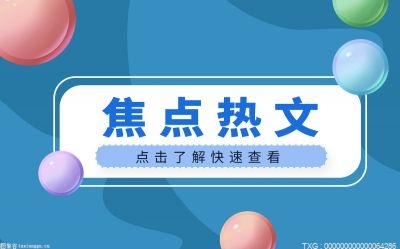

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
營業執照公示信息